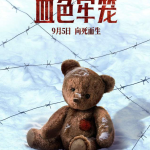在年代剧创作中,人物塑造往往容易陷入 “非黑即白” 的脸谱化困境 —— 要么是完美无缺的英雄,要么是十恶不赦的反派。而《生万物》最难得的突破,便在于它以细腻的笔触,勾勒出一张张充满人性褶皱的面孔,让每个角色都跳出 “标签化” 的束缚,成为既有优点也有缺陷、既会挣扎也会成长的 “真实普通人”,这种对复杂人性的深度呈现,也让整部剧的现实主义质感愈发厚重。

宁学祥的转变,堪称剧中 “人性复杂” 的典型注脚。开篇的他,是个不折不扣的 “守财奴”—— 视土地与家产高于一切,女儿宁绣绣遭遇绑架时,他最先顾虑的不是女儿安危,而是 “赎金会掏空家底”;面对村民的困境,他也始终抱着 “各扫门前雪” 的冷漠态度,身上带着旧时代地主阶层的自私与固执。但随着剧情推进,当日军与反派 “腻味” 威胁到全村人的性命时,他内心的良知被逐渐唤醒:主动献出存粮拯救饥民,将世代相传的土地分给村民,甚至在关键时刻放下 “大家长” 的身段,听从晚辈的建议共同抗敌。他的转变不是突兀的 “洗白”,而是在时代洪流与现实困境中,人性中 “善” 与 “私” 的反复拉扯 —— 他曾被利益裹挟,却从未彻底泯灭良知,最终在大义面前完成了自我救赎。观众看到的,不是一个 “突然变好” 的地主,而是一个在挣扎中逐渐认清 “家国大义重于个人私利” 的普通人,这种真实的转变,远比 “完美英雄” 更能打动人心。
费左氏的人物弧光,则更具悲剧性与复杂性。她既是旧时代封建礼教的 “受害者”——18 岁嫁入费家便守寡,独自撑起家族重担,一生被 “传宗接代”“家族规矩” 的枷锁捆绑;却又在长期的压抑中,变成了封建礼教的 “维护者”—— 固执地认为宁苏苏 “生是费家人,死是费家鬼”,即便对方早已挣脱束缚,也不愿接受现实。她的 “恶” 并非天生的坏,而是被时代与观念扭曲的执念:费文典的牺牲击碎了她的精神支柱,宁苏苏的幸福又刺痛了她的不幸,最终在绝望与嫉妒中走向极端,酿成毒杀他人后自杀的悲剧。观众对她的情感,从来不是简单的 “痛恨”—— 既同情她被封建礼教吞噬的一生,也惋惜她因执念毁掉他人与自己的命运,这种 “又怜又恨” 的复杂情绪,恰恰印证了人物塑造的成功。

除了核心角色,《生万物》中的配角也同样鲜活立体。封二身上带着小农的 “烟火气”—— 会为了几分地与邻居争执,会因一点小利斤斤计较,却在关键时刻守住 “大义”,临终前还不忘将种地经验传给家人,他的 “小毛病” 与 “大格局” 并存,活脱脱就是现实中常见的农民形象;铁头的人生则充满 “成长的挣扎”—— 起初因怯懦错失爱情,后来因权力迷失自我,却在与傻桃、坷拉的相处中唤醒善良,最终在抗敌中展现勇气,他的每一次犯错与改正,都像极了普通人在人生路上的跌撞前行;郭龟腰的 “机智与善良” 也并非刻意塑造 —— 他会用小聪明化解危机,也会在危难时挺身而出,即便劫后余生、即将收获幸福时意外离世,也让观众记住了这个 “有血有肉的好人”。

这些角色没有统一的 “完美模板”,却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社会图景 —— 有地主的转变,有农民的坚守,有女性的挣扎,有青年的成长。他们的喜怒哀乐、得失成败,都是时代浪潮中普通人的真实写照。观众在剧中看到的,不是 “理想化的英雄叙事”,而是 “接地气的人性百态”—— 会为宁学祥的救赎欣慰,会为费左氏的悲剧叹息,会为封二的烟火气会心一笑,也会为铁头的成长由衷点赞。这种 “感同身受” 的共鸣,正是《生万物》在人物塑造上最成功的地方:它不回避人性的缺陷,也不夸大人性的光辉,只是真实地呈现 “人” 本该有的样子,而这份 “真实”,恰恰是年代剧最珍贵的品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