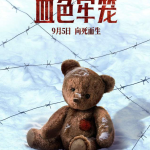打开脱口秀综艺,如今总让人陷入两种困境:一是时长膨胀,一期节目拆分三四集,即便纯享版也得耗上一部电影的时间;二是内容趋同,穷、职场、学历等话题反复出现,选手们像是拿着同一份 “考题” 在不同演播厅作答。从 2017 年《脱口秀大会》首播至今,这个行业在八年里完成了从 “向外探索” 到 “向内凝视” 的转向,好笑依旧,只是那股捅破窗户纸的锐利,似乎淡了些。


早期脱口秀的魅力,在于对社会肌理的敏锐捕捉。某演员描摹的司机形象,藏着城市化进程中的世情百态;杨蒙恩一句 “遍地是大王,短暂又辉煌”,道尽新兴行业的泡沫;何广智笔下 “地铁挤到双脚悬空刷手机” 的场景,更是成了生存韧性的生动隐喻。那时的段子像广角镜头,总能在个人经验里照见群体共鸣,哪怕是思文 “夫妻成兄弟” 的调侃、张博洋对键盘侠的吐槽,也都带着对生活本质的拆解。
如今的脱口秀,更像切换到了微距模式。《喜剧之王单口季 2》里,大老王精确计算着 8 点 59 分打车与 9 点打车的差价,徐指导细数爷爷被缅北诈骗的种种细节;《脱口秀和 Ta 的朋友们 2》中,呼兰用一整期讲本命年禁忌,锐锐纠结于城里女友对农村生活的想象。这些观察细致到近乎琐碎,如同张爱玲说的 “观察自己的肚脐眼”—— 人们或许会惊呼 “我也是这样”,却难再有 “原来大家都这样” 的通透。


议题的收窄并非偶然。穷、职场、学历、性别等话题的密集出现,既是社会压力下的情绪释放,也暗含着娱乐工业的安全策略。有人说这是填补了表达真空,比如女性演员对痛经、职场性骚扰的直白讲述,比八年前柳岩在台上承受的恶意调侃进步太多;也有人觉得是投机取巧,毕竟 “中专梗”” 穷门永存 ” 之类的标签,容易形成记忆点却也陷入同质化。
其实争议的核心,不在话题大小,而在文本质量。同样讲女性议题,房主任的离婚叙事能让观众泪奔,小帕的创伤讲述却让人陷入笑与不笑的纠结;同样聊学历,小奇用 “中专生鱼妹” 的巧思打破刻板印象,有些选手却只靠重复标签凑数。当 “小我叙事” 沦为套路,再热的话题也会失去力量。


脱口秀本就是时代的镜子,从广角到微距的切换,照见的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变化 —— 当向外探索的路遇阻,便转而在向内凝视中寻找共鸣。只是镜子若只照肚脐眼,再精致的描摹也会失了格局。或许正如行业需要的,不是回到过去的宏大,而是在细微处保持锐度,让每个 “小我” 的故事里,都藏着能让众人会心一笑的 “大世界”。